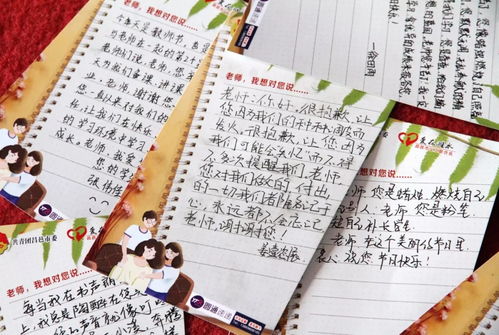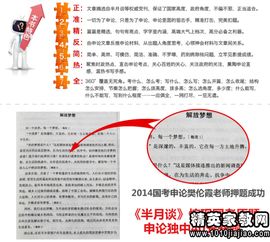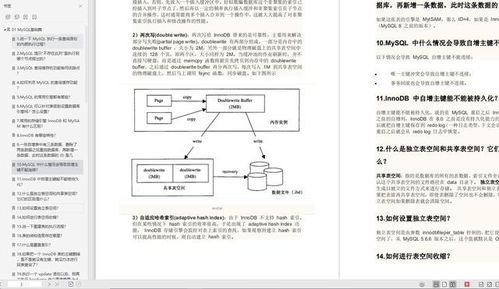文/李俊英

冬夜的风刮得格外猛烈,把窗户纸吹得哗哗作响。五个孩子挤在土炕上,每个人手里都捧着一个泛黄的葫芦瓢,里面堆着小山似的带壳花生。母亲坐在煤油灯旁,一边麻利地剥着簸箕里的花生,一边用温软的声音说:"今晚咱们讲三兄弟遇见蜥蜴精的故事。"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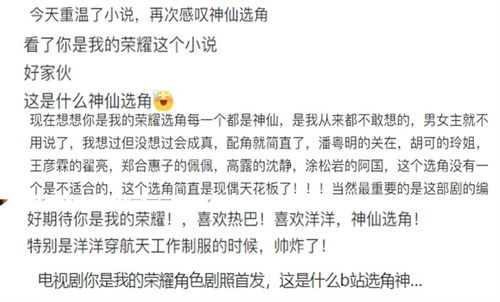
煤油灯芯爆出个灯花,墙上的影子跟着晃了晃。大哥的瓢里永远整整齐齐码着白胖的花生仁,二哥的瓢总混着壳和仁,要到最后才手忙脚乱地分拣。我习惯把仁和壳分开放,三哥闷声不响剥得最快,小弟装模作样抓着花生往嘴里塞。花生壳碎裂的脆响里,母亲的声音像条温暖的溪流,带着我们漂进那个神奇的世界。
故事要从三兄弟在地头歇晌说起。烈日把锄头柄晒得发烫,三个后生轮流对着陶罐喝水。前两次蜥蜴趴在罐口都被赶走,轮到老三时,他摘片桑叶舀水喂了那小东西。后来三匹神马驮着他们来到枯井前,只有老三在井底遇见了梳妆的姑娘。母亲讲到姑娘递出宝刀时,窗外的北风正卷着枯叶打旋,小弟手里的花生仁撒了一炕。

当老三误骑黑羊坠入九重天时,灶膛里的柴火"噼啪"炸响。我们屏住呼吸听他在黑暗里摸索,直到他循着哭声走进那户愁苦的人家。母亲描述蛟龙被斩的场面时,二哥不小心掐碎了手里的花生仁,油渍在瓢底洇出个月牙印。
最惊心动魄的是大野猪撞断古树那段。母亲突然提高声调,惊得煤油灯焰猛蹿了下。当鸟妈妈驮着老三穿越云层时,小弟已经歪在我肩上打起了瞌睡。老三割肉喂鸟的情节让我攥紧了葫芦瓢,直到听见新娘在村口等待的结局,才发现手心全是汗。

四十多年过去,那个总把花生壳掉进仁堆里的二哥成了儿科医生,闷头剥花生最认真的三哥在海关工作。去年冬至全家团聚时,白发苍苍的母亲又说起这个故事,阳光透过新装的玻璃窗,把装花生的不锈钢盆照得明晃晃的。小弟突然问:"当年那只蜥蜴,是不是故意考验三兄弟的?"母亲笑着往他手里塞了把花生:"你说呢?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