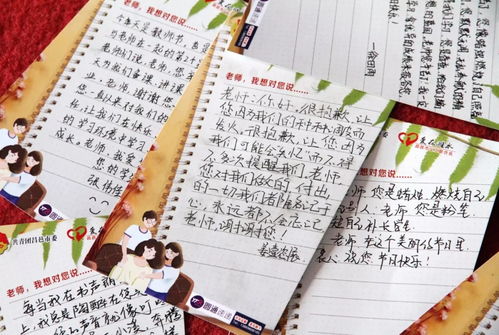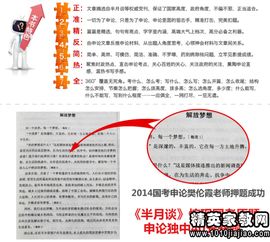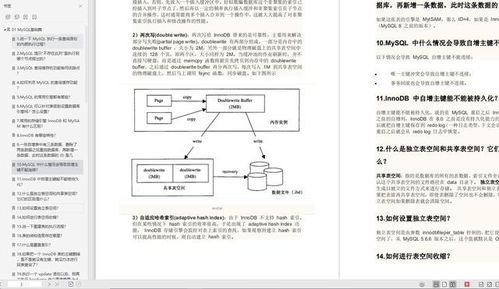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清晨,我背着书包走在去学校的路上。前夜刚下过雪,路面结着薄冰,我踩着咯吱作响的积雪,呼出的白气在围巾上结出细小的冰晶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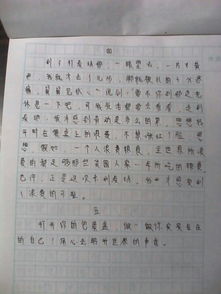
第二节下课铃响后,我们像往常一样到操场晨跑。跑着跑着,突然觉得双腿发软,眼前一阵阵发黑。同桌小林发现我脸色苍白,急忙扶我去医务室。校医一量体温:39.2℃。我这才意识到,早上出门时头重脚轻的感觉不是没睡醒。
班主任给妈妈打了电话。不到二十分钟,我就看见她气喘吁吁地出现在医务室门口,发梢还沾着雪花。她蹲下来摸了摸我滚烫的额头,二话不说就背起我往医院走。趴在妈妈瘦弱的背上,我能感觉到她每走一步都在微微发抖。
打针时我死死攥着妈妈的衣角,护士阿姨笑着说:"小伙子要勇敢呀。"妈妈把我的手握在掌心,她的手冰凉却有力。回家路上,她一直用围巾裹着我的耳朵,自己却冻得鼻尖通红。那晚我迷迷糊糊醒来好几次,每次都看见妈妈坐在床边,就着台灯微弱的光给我擦汗。
现在想来,那个冬天最温暖的记忆,不是热乎乎的糖炒栗子,而是妈妈背着我走过风雪时,落在她睫毛上的雪花。
去年深秋,我在公交站台遇见一位盲人爷爷。他拄着拐杖,脚边放着装满手编篮子的竹篓。突然下起大雨,路人纷纷撑伞跑开,老人摸索着往屋檐下挪动时,一个穿校服的女孩冲进雨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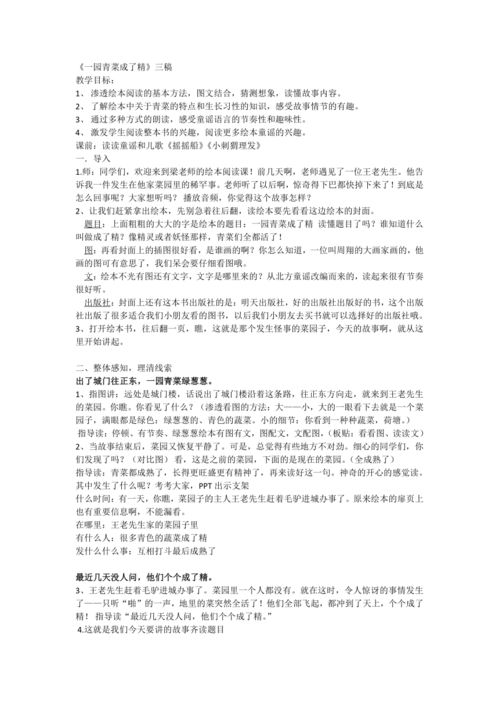
她一手扶着老人,一手高高举着书包挡在老人头顶。雨水顺着她的马尾辫往下淌,校服外套很快湿透了。等我把伞撑过去时,听见老人不停念叨:"闺女你快回去,我这老骨头淋点雨不打紧。"
女孩固执地摇头,直到把老人送到附近的杂货店屋檐下。店主递来毛巾时,我才发现她左臂戴着"文明监督员"的袖章。她拧干衣角的水,笑着说:"下周运动会要用的班费还差些,这些篮子我全要了。"
后来每次路过那个站台,我总会想起雨中那个挺得笔直的背影。原来有些光,不需要眼睛也能看见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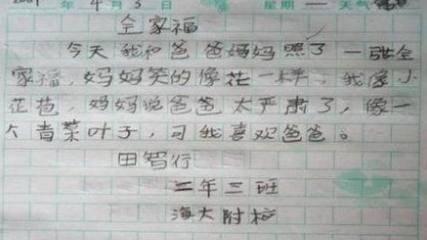
小区门口的修车铺王师傅有双粗糙的大手。去年夏天暴雨过后,我在他铺子前看见个浑身湿透的小男孩,正对着掉链子的自行车掉眼泪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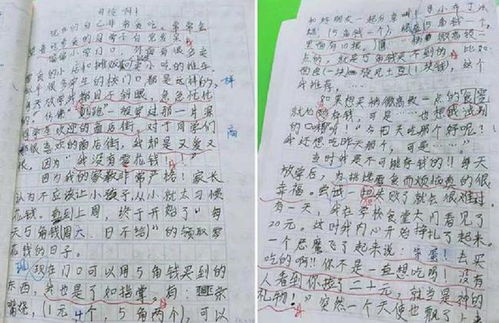
王师傅蹲在男孩面前,用扳手轻轻敲了下车轮:"男子汉哭什么?来,我教你个绝活。"他布满老茧的手指灵活地拨弄着链条,油污混着雨水在脸上画出一道道黑线。男孩学着他的动作,终于把链条装回去时,两人同时笑出一口白牙。
第二天我去取车,发现王师傅正在修一辆生锈的童车。"隔壁巷子小囡的,她爸爸住院了。"他头也不抬地说。后来我才知道,他抽屉里有个笔记本,记满了赊账修车的孩子名字,后面都画着小小的对钩。
现在每次听见"叮叮当当"的修车声,我都会想起那双沾满油污却格外温暖的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