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橘颂:致张枣》是诗人柏桦为故友张枣写下的文字,但它更像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。这本书里藏着诗人之间的秘密,有对旧友的思念,也有对诗歌的重新诠释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里感叹知音难觅,千百年来能称得上知音的,大概只有俞伯牙与钟子期,或是李白与杜甫那样的情谊。杜甫对李白的仰慕藏在诗句里,而柏桦与张枣的交往,则让知音这个词有了更鲜活的注解。
《橘颂:致张枣》,作者:柏桦,版本: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2年3月
柏桦比张枣大六岁,两人更像是同代人。他们互相欣赏,用文字记录彼此。这种知音般的默契落在纸上,成了诗歌的秘密,也成了时代的见证。书里不仅有对诗歌的探讨,更藏着两个诗人如何用语言搭建起一座桥梁。
1999年冬,柏桦与张枣(右)。

“橘子的气味弥漫着聪慧”
柏桦用屈原的《橘颂》作为书名,橘树在诗里是品格的象征,而在张枣的诗中,橘子成了诗意的化身。张枣写橘子,柏桦看出其中的乡愁,也看出他与楚地诗歌的血脉相连。张枣的诗里有南方的声音,既承接了《楚辞》的神秘,又在现代白话里找到新的韵律。他的《何人斯》改写自《诗经》,却把政治诗变成了情诗,追问的不仅是人心,还有存在的意义。
柏桦说张枣的诗总在探索人称之间的关系,而《何人斯》里的“你”和“我”,正是诗歌最本质的对话。张枣的诗轻盈却深邃,他能从具体的故事里抽身,直指普遍的诗性真理。这种能力让他的诗既扎根传统,又充满现代感。柏桦提到,张枣在信里常谈诗的戏剧性、语言的锤炼,后来这些思考成了他的“元诗”理论。

张枣的元诗观念来自东西方的双重滋养。他相信语言有创造的力量,像上帝说“要有光”一样,诗人用词语构建世界。柏桦的书写揭示了这种诗学的中西交融,张枣的诗既回望古典的甜,又纠正了西方现代诗的孤绝。汉学家顾彬说张枣是中国送给德国的礼物,正因为他的诗在两种文化间自由穿行。
1986年初秋,张枣在德国,此照片背面写有一句话——“另一个骑手……柏桦惠存”
“谈心的橘子荡漾着言说的芬芳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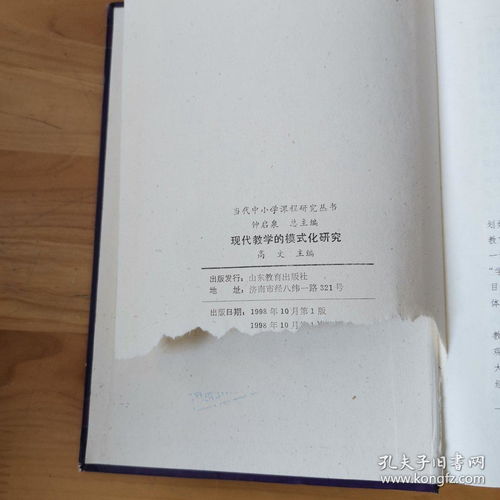
《橘颂:致张枣》分为四部分,从诗学论文到追忆文字,再到写给张枣的诗,全书弥漫着对话的气息。张枣擅长在诗里设置对话,而柏桦的这本书,正是这场对话的延续。张枣曾把他们的见面称为“谈话节”,说每次见面要说好几吨话,直到精疲力竭。柏桦在书里提到,张枣用“谈话疗法”形容他们的交流,语言成了治愈的方式。
张枣的诗里常有“词语织布机”的意象,比如《悠悠》中“每个人嘴里都有一台织布机”,语言在这里成了分享诗意的工具。柏桦认为张枣的诗超越了精神分析的范畴,语言不是投影,而是生命的本质。在《椅子坐进冬天》里,张枣写道:“语言才是我们的主人”,这种对语言的信仰贯穿了他的创作。

1987年冬,张枣首次回国,与部分圈内朋友合影。后排左起:杨伟、郑单衣、邱海明、刘波、李伟;前排左起:傅维、平凡、张枣、柏桦
“你熟睡如橘”
《橘颂:致张枣》记录了一段诗歌友谊,也展现了柏桦的文学眼光。他说“颓废之甜才是文学的瑰宝”,这种对消逝之美的敏感,正是诗人的特质。书里偶尔透出的禅意,与生死主题相呼应,却又落在对日常的关注上。
布罗茨基说“时间是节奏的源泉”,而这本书正是时间的重构。柏桦的文字时而松散时而浓烈,为张枣招魂的段落甚至带着诗性的错乱。《橘颂》最接近儒家诗教的精神,而张枣的诗里也有君子的品格。柏桦提到诗人互相修改作品,是让彼此的文字更精确,这种对话超越了生死。这本书在一个匆忙的时代里,用缓慢的笔调留住了一段青春与诗意的记忆。
文/王东东
编辑/张进
校对/薛京宁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