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到爱的距离》剧照

医药代表这个职业总带着些难以言说的尴尬。每当有人问起工作,我总是含糊其辞地应付过去,仿佛这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。

毕业那年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,一边是父母安排好的医院工作,一边是遥不可及的摄影梦想。在又一次争吵后,我拖着行李箱来到上海,才发现医疗专业的就业面竟如此狭窄。投出去的简历石沉大海,直到看见医药代表的招聘信息——既不用去医院,又能暂时解决生计问题。

面试时HR问我有什么问题,我怯生生地问:"这个工作具体是做什么的?"对方愣了一下:"就是和医生打交道的。"这个模糊的回答,成了我踏入这个行业的开端。
入职培训更像是一场大型洗脑现场。梳着油头的讲师在台上高谈阔论,我们每天要集体喊口号"我最棒"。父亲收到公司寄来的家书时,差点以为我进了传销组织。直到第五天才接触到实质内容——如何分门别类地应对不同类型的医生。
初到上海分公司的场景至今记忆犹新。老旧的五楼宿舍里,铁架床吱呀作响,客厅只有一张泛黄的木桌。但听到"出差"二字时,我还是忍不住心生向往。后来才明白,所谓的出差不过是陪医生游山玩水的借口。
第一次跟师傅去医院拜访,清晨六点的医院走廊已经排起长队。看着师傅熟稔地和医生寒暄,关门时我瞥见白大褂里闪过信封的踪影。那天我们跑了四五家诊室,下午在高档餐厅开了张"招待客户"的发票——这后来成了家常便饭。
独立拜访客户时,手心总是汗涔涔的。遇上好说话的郝医生是运气,更多时候面对的是冷若冰霜的刘医生。师傅说这种"潜力客户"需要下血本,周末得提着海鲜上门拜访。渐渐地,我学会了察言观色:水果饮料要藏在包里,见到可疑人员要立即撤离,从只言片语中揣摩医生的喜好。
月末核算用药量时,我才真正接触到那个神秘信封。电脑拍下的用药表格需要手工统计,每个信封里的数字都精确计算。递信封时要记得关门,聊旅游时要适时提议"学术会议"——新疆的草原,三亚的海滩,这些临时编造的会议成了最好的由头。
但总有些医生不吃这套。陈医生拒绝所有医药公司的拜访,坚持只开对患者真正有效的药。看着同事不屑的表情,我忍不住怀疑:如果我们推广的真是好药,为什么需要这样费尽心机?
转正前夕,同期入职的朋友辞职了。她说每天编造话题太痛苦,这份工作让她失去坦荡的底气。评选会上经理保证我能转正时,我突然说:"我想辞职。"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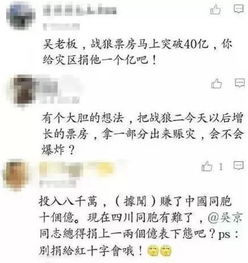
四个月的医药代表生涯像一场荒诞的梦。医生和药品之间本该是清澈的桥梁,如今却成了见不得光的地下交易。也许某天,这个职业能真正光明正大地存在,让从业者可以昂首挺胸地说出自己的职业。但至少现在,我还做不到。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