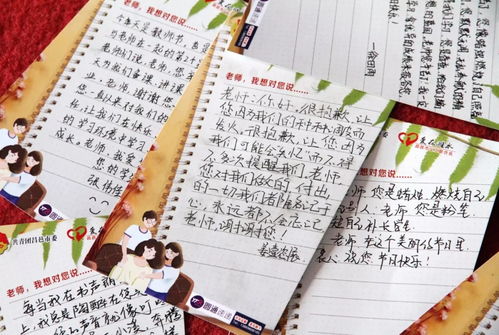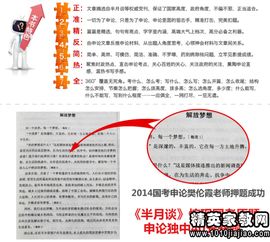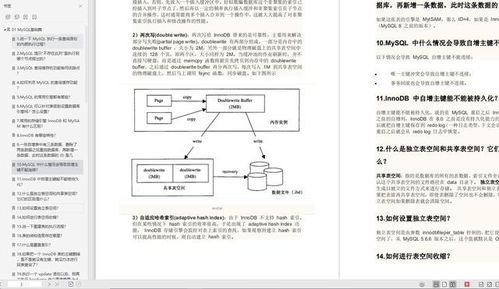五月的风裹着槐香拂过脸颊时,我突然在岔路口停住了脚步。这条新铺的柏油路泛着青黑的光泽,两旁整齐的槐树苗才抽到手腕粗,枝叶倒是茂密,在风里沙沙摇晃着绿浪。
树梢头零星挂着几串青白花苞,像被谁随手别上去的银铃铛。我仰头看了许久,到底没等到它们齐齐绽放的时刻。雨丝忽然斜斜地飘下来,在相机镜片上撞成细碎的水花,想象中的《烟雨槐花图》终究没能拍成。
记忆里的槐树从来不懂什么叫规整。它们总歪在土墙根、沟渠边,树皮皲裂如老人手背的皱纹。可春风路过时,这些不起眼的枝桠便魔术般抖出满身翡翠,眨眼间又缀满米粒大的花苞。某天清晨推开门,整棵树突然炸开千万朵白蝴蝶,闹嚷嚷挤满枝头,甜香能撞人一个跟头。
最鲜活的光景要数孩子们捋槐花的时节。瘦猴似的黑娃骑在树杈上,汗津津的小腿被树刺划出红道子也浑不在意。咔嚓的折枝声里,青白花穗簌簌落进竹篮,惊起一地欢叫。他们跑远后,只剩断枝残叶在风里轻轻打颤,像被扯破的蛛网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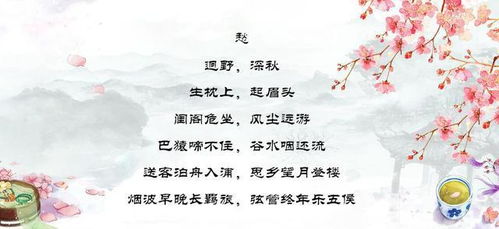
面粉裹着的槐花在蒸笼里渐渐变得晶莹剔透时,香气会顺着没有围墙的院落流淌。东家西户的粗瓷碗在炊烟里来回传递,最后连碗底的面水都要舔得干干净净。五月的光阴就这样被嚼得满口生香,连打出的饱嗝都带着阳光的味道。
如今站在新栽的槐树苗下,雨幕模糊了远处的山影。忽然明白有些热闹就像槐花,轰轰烈烈开过一季,便永远留在某个泛黄的五月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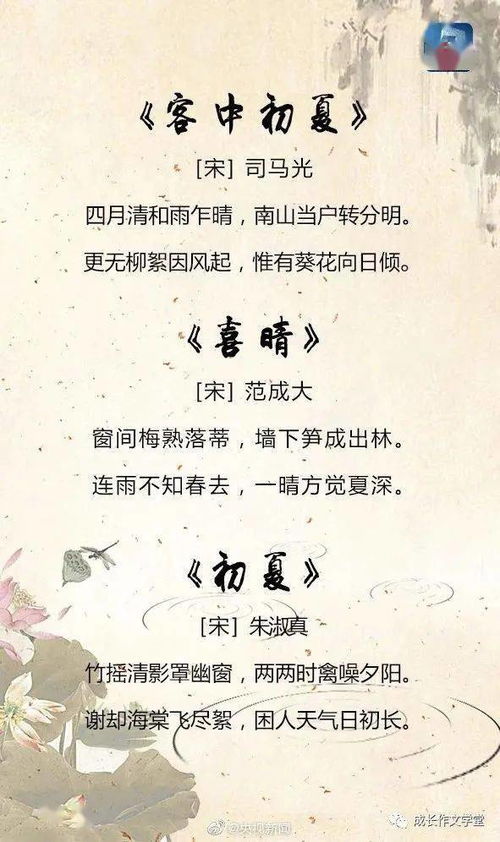
十月的天空蓝得发脆,仿佛轻轻一碰就会叮当作响。丽江古城的石板路被岁月磨成了镜面,倒映着穿冲锋衣的游客和纳西老人脸上的沟壑。酒吧街的吉他声与三弦琴在巷口狭路相逢,最终都消融在四方街的篝火星光里。
窗台上的玫瑰趁着夜色偷偷绽放时,电脑里突然淌出那首老歌。我愣在沙发里,看记忆像退潮后的沙滩,露出许多被遗忘的贝壳。年轻时总爱把成熟当盔甲,后来才懂,真正坚固的东西从来不需要伪装。
深秋的田野裸露出最原始的肌理。收割后的稻茬排列成神秘符号,偶尔有田鼠窜过,惊起两三只捡食的麻雀。拾粪老人弯腰的弧度与土地保持着惊人的默契,他的布鞋踩过的地方,霜花悄悄融化成清晨的露水。
城市公园的柳絮开始年度迁徙时,小女孩追着其中一朵跑了半片草坪。她不知道这些飞絮最终会落在哪个角落,就像我们永远猜不透,巷子深处那株野菊花是如何在石缝里攒够绽放的勇气。

雨后的溪水漫过青石板,捶衣声惊醒了睡在芭蕉叶上的阳光。当月光洗亮整条山涧,男人和女人的笑骂声便随着水花溅湿了半个村庄。这些潮湿的记忆,多年后仍在某个失眠的夜里淅淅沥沥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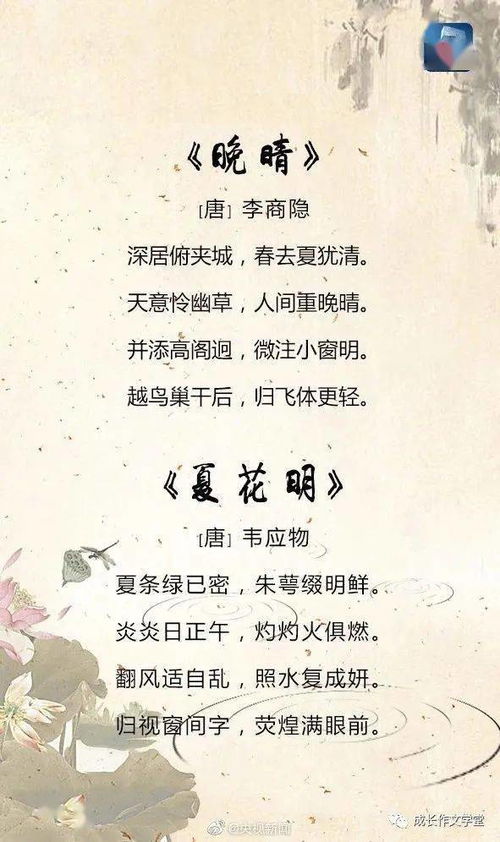
所有空旷都有回声。秋风翻过最后一道田埂时,稻草人突然抖了抖空荡荡的衣袖。它守着的不是庄稼,而是土地与天空之间,那段用寂静丈量的时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