夜晚像一艘熄了灯的船,静静漂浮在黑暗里。船身与现实之间,始终隔着一层薄薄的距离。岸上的人声鼎沸,公园里挤满喧嚣的人群,而船上的人独自守着这份寂静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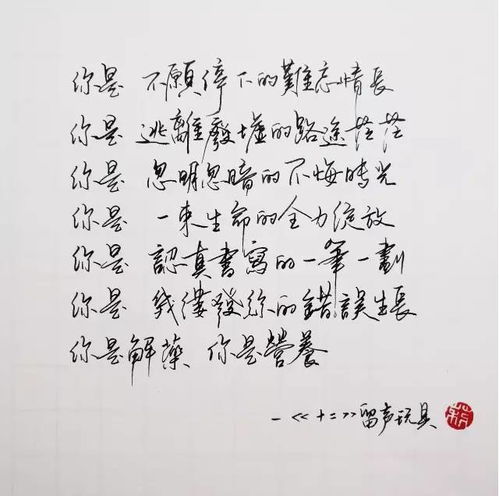
二月的雪总让人想起许多事。旧历二月初,二爷的葬礼在飘雪中进行。他从腊月就卧病在床,所有人都等着那一刻到来。当他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,亲戚们反倒松了口气——要是赶在过年期间,该有多麻烦。他们说这是解脱,对他好,对大家都好。
遗照用的是他生前唯一一张照片。照片里,他站在邻居家的面包车旁,腰板挺得笔直。黑棉袄用布带扎着,棉裤松松垮垮地套在腿上。他咧着嘴笑,露出光秃的牙床,神情有些腼腆。
这个打了一辈子光棍的老人,生前寄居在弟弟家,活得像个影子。直到死后,才第一次成为主角。侄子侄女们披麻戴孝,远房亲戚也赶来吊唁。弟弟请来的唢呐班子吹了三天三夜,曲调忽悲忽喜,给葬礼添了几分热闹。
出殡那天下起雪来。白色的送葬队伍抬着黑棺材,在雪中缓缓移动,像电影里的长镜头。等到了坟地,挖掘机的轰鸣打破了肃穆的气氛。女人们开始说笑,活人之间的关系因为死亡而变得更亲密。雪不知什么时候停了,返程时大家脱下孝服,脚步轻快地往回走,死亡早已被抛在脑后。
我对二爷没什么感情,但他的死确实成了记忆里的一部分。村里不断有人离开,活着的人把他们埋掉,日子照常继续。死亡本该教会我们什么,可谁又真正记住了这些教训?
韩愈写春雪,说它像顽皮的孩子,嫌春天来得太晚,故意在树间穿梭嬉戏。这首诗简单直白,雪就是雪,没有太多深意。古人看世界的眼光纯粹,词语直接指向事物本身。如今我们早已习惯赋予万物象征意义,反而失去了这种质朴。

刘方平的《春雪》别有韵味。前两句写飞雪在春风中舞动的姿态,后两句笔锋一转:"君看似花处,偏在洛城东。"雪本无差别,落在富人区和贫民窟却是两种景象。富贵人家赏雪是雅事,穷人在雪天只能发愁如何取暖。这种对比含蓄而深刻,比直白的批判更有力量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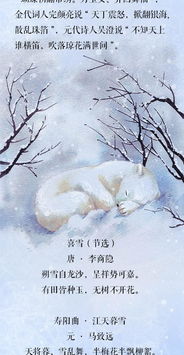
温庭筠笔下的三月雪带着暮春的温柔。梨花盛开时,最后一场雪悄然降临,像是春天临别的礼物。但现实往往没这么诗意。记得有年三月,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冻死了整片果园的花,农民们站在地头,看着一年的希望化为乌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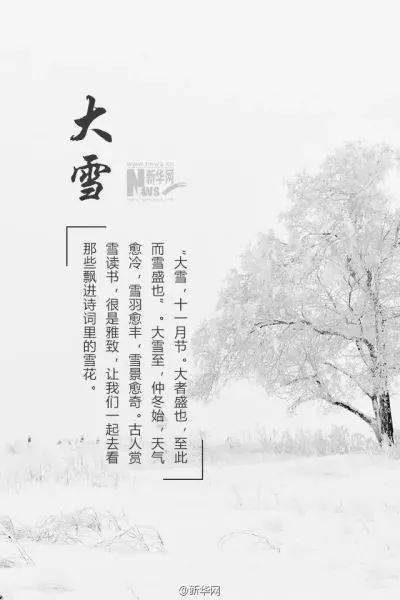
我出生在北方的冬天,寒冷早已刻进骨子里。后来搬到南方,以为能逃离严冬,却发现心里的冬天从未消失。雪总让我想起葬礼,想起人世间种种无奈。我们活着到底为了什么?这个问题或许没有答案,但值得一直追问。
诗歌给我们片刻自由,却改变不了什么。就像一场大雪,除了提醒生命终将消逝,还能带来什么慰藉?










